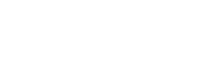情与辞
2020/06/29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显著的如喜、怒、爱、恶、哀、愁等情绪,微妙的如兴奋、颓唐、忧郁、宁静以及种种不易名状的飘来忽去的心境。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文字有言情、说理、叙事、状物四大功用,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若不然,那就成为枯燥的没有生趣的日常应用文字,如帐簿、图表、数理化教科书之类。不过这种界线也很不容易划清,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是容易为理、事、物所触动的。许多哲学的、史学的甚至于科学的著作都带有几分文学性,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不运用言辞则已,一运用言辞,就难免要表现几分主观的心理倾向,至少也要有一种“理智的信念”,这仍是一种心情。
情感和思想通常被人认为是对立的两种心理活动。文字所表现的不是思想,就是情感。其实情感和思想常互相影响,互相融会,除掉惊叹语和谐声语之外,情感无法直接表现于文字,都必借事理物烘托出来,这就是说,都必须化成思想。这道理在中国古代有刘彦和说得最透辟。《文心雕龙》的《熔裁》篇里有这几句话:“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
用现代话来说,行文有三个步骤,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种情致,其次要找出具体的事物可以烘托出这种情致,这就是思想分内的事,最后要找出适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情思化合体表达出来。近代美学家克罗齐的看法恰与刘彦和的一致。文艺先须有要表现的情感,这情感必融会于一种完整的具体意象(刘彦和所谓“事”),即借那个意象得表现,然后用语言把它记载下来。
我特别提出这一个中外不谋而合的学说来,用意是在着重这三个步骤中的第二个步骤。这是一般人所常忽略的。一般人常以为由“情”可以直接到“辞”,不想到中间须经过一个“思”的阶段,尤其是十九世纪浪漫派理论家主张“文学为情感的自然流露”,很容易使人发生这种误解。在这里我们不妨略谈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和分别。艺术原义为“人为”,自然是不假人为的,所以艺术与自然处在对立的地位,是自然就不是艺术,是艺术就不是自然。说艺术是“人为的”就无异于说它是“创造的”。创造也并非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艺术所本。艺术根据自然,加以熔铸雕琢,选择安排,结果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换句语说,自然须通过作者的心灵,在里面经过一番意匠经营,才变成艺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全在“自然”之上加这一番“人为”。
这番话并非题外话。我们要了解情与辞的道理,必先了解这一点艺术与自然的道理。情是自然,融情于思,达之于辞,才是文学的艺术。在文学的艺术中,情感须经过意象化和文辞化,才算得到表现。人人都知道文学不能没有真正的情感,不过如果只有真正的情感,还是无济于事。你和我何尝没有过真正的情感?何尝不自觉平生经验有不少的诗和小说的材料?但是诗在哪里?小说在哪里?浑身都是情感不能保障一个人成为文学家,犹如满山都是大理石不能保障那座山有雕刻,是同样的道理。
一个作家如果信赖他的生糙的情感,让它“自然流露”,结果会像一个掘石匠而不能像一个雕刻家。雕刻家的任务在把一块顽石雕成一个石像,这就是说,给那块顽石一个完整的形式,一条有灵有肉的生命。文学家对于情感也是如此。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在沉静中加过一番回味,情感才由主观的感触变成客观的观照对象,才能受思想的洗炼与润色,思想才能为依稀隐约不易捉摸的情感造出一个完整的可捉摸的形式和生命。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这一番话是偏就作者自己的情感说。从情感须经过观照与思索而言,通常所谓“主观的”就必须化为“客观的”,我必须跳开小我的圈套,站在客观的地位,来观照我自己,检讨我自己,把我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行动姿态当作一幅画或是一幕戏来点染烘托。古人有“痛定思痛”的说法,不只是“痛”,写自己的一切的切身经验都必须从追忆着手,这就是说,都必须把过去的我当作另一个人去看。我们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态度。明白这个道埋,我们也就应该明白在文艺上通常所说的“主观的”与“客观的”分别是粗浅的,一切文学创作都必须是“客观的”,连写“主观的经验”也是如此。
但是一个文学家不应只在写自传,独角演不成戏,虽然写自传,他也要写到旁人,也要表现旁人的内心生活和外表行动。许多大文学家向来不轻易暴露自己,而专写自身以外的人物,莎士比亚便是著例。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心理变化在他们手中都可以写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会设身处地去想象,钻进所写人物的心窍,和他们同样想,同样感,过同样的内心生活。写哈姆雷特,作者自己在想象中就变成哈姆雷特,写林黛玉,作者自己在想象中也就要变成林黛玉。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就应该明白一切文学创作都必须是“主观的”,所写的材料尽管是通常所谓“客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假如名人来高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