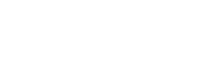烟灭与万有引力
2020/08/10烟灭与万有引力辽宁/葛桂林李老师非常喜欢我。李老师教语文,我是语文尖子生。他虽然是代课教师,但他酷爱文学,说酷爱,只是我当时一个新鲜的名词,反正他写了一篇小说,给贾伟和我看了,我们都说好!‘好在哪呢?我也忘了,甚至连小说的名字也忘了,只记得他把小说署名:李伟林。分别占我们名字里的一个字。他说。文章一但见刊,算我们三个的,我们不属外。是啊,我们虽然称他老师,在同…村住不说,又是同龄人。当时我们市文联只出一种双月刊《朝阳》,我们一遍遍地读完老师的稿子再添枝加叶地修改,足足费了好几天时间,他却说不好,再看他屋的纸篓里全是草稿。老师说,我们还小,没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像大林你吧。喜欢诗歌就写点诗歌吧。那报纸不是登了诗歌吗?我脸红红的,那是什么诗歌啊?排列在一起就是散文,太直白了。老师鼓励我说,你还是中学生啊,《我是个农民的儿子》写得已经十分了得?贾伟凑趣地起哄:还了得?然后就偏着脸,讪讪地朗诵那首诗,我就憋红了脸追他,心说,你是嫉妒还是嘲弄?贾伟读着,跑开了,嘻嘻笑着,大林,我是为你高兴呢,你这是做什么?贾伟不跑了,立刻站住,我扑到他怀里,差点扑倒。贾伟说:李老师,我还写了一首诗歌呢,你听听能不能登报?他就背诵起来:小河弯弯/垂几株细柳/拂一个小小山村/牧牛郎的鞭声/脆脆地从树丫滑落/抽响一川翠绿的虫鸣/7甩出一池银白的鸭音/柳丛深处/淌出…阵悠扬的唿哨/惹得洗衣姑娘低下头/揉碎一河焦灼的目光……李老师和我都张大嘴巴伸长耳朵听着.那嘴张得像驴嘴,耳朵像猪耳朵,虽然开始听得不屑一。顾,后来便傻眼了,我竖起大拇指,老师上去就擂打贾伟的双肩,你小子,行啊!写得真好!贾伟背靠一颗歪脖子柳树,得意洋洋晃动大脑袋继续背,太阳斜射过来,透过柳丝抚摸着他的头发,暖暖的,我突然看到他们两个人发黄的手指。李老师说,来。大林,坐柳树墩上歇歇.老师就依偎在柳树的旁边。这是一颗怀抱粗的柳树,根部隆起了.课间老师学生经常来这里纳凉。我们三个好友也是经常聚在这里谈诗歌,小说。老师猫腰吹吹柳树根上的土,用手扑拉扑拉,倚着树干坐了下去。我说:老师,树根上竟是土,脏啊。老师很会说,土算什么?你没听说过,人吃土欢天喜地,没事。老师不比我们大,却是地地道道的烟民了……李老师坐稳了,我坐在他身边看着贾伟背诗歌,贾伟却戛然而止。掏出一本烟纸来。那自白的烟纸,顶部鲜红鲜红的,有阳光在上面闪耀。老师下意识地摸摸口袋,其实,什么也没有。我们都是孩子。虽然二十岁上下。也是孩子。我们没有钱去买卷烟.小时候.就找那发黄的转莲(向日葵)叶子放到阳光下晾晒,妈妈问我们作甚?爸爸有时候警觉了我要学抽烟,就拍打我屁屁说,我们祖辈都不吸烟,你要学好啊……我虽然不服气,但不做声了。对抽烟不上瘾,不像贾伟和李老师,下课就偷偷地卷转莲叶子。他憋得酱紫的脸,在学校的旮旯一口口地吐黄痰,嘴里丝丝地,辣啊,辣……能不辣吗?转莲叶子我抽过.呛得我眼泪都下来过。他们最憋不住的是,那些日子学校老师抓抽烟的,他们躲到厕所里抽。这时,贾伟把烟纸拧成一个白色喇叭,笑着对老师说.我这里有烟?老师很惊喜,烟?什么烟?老蛤蟆。嗨!老师的手拍在柳树根上,不还是转莲叶子吗?拍完了。说完了,还是伸长发黄的手指。李老师,我给你搓了,卷了。天真是好,一丝风都没有。垂柳依依的像大姑娘的披肩发,静静地低垂着,注视着我们三人。这时我倒想有一阵风吹过来,把贾伟放到地上的两个白色喇叭筒吹起来,像飘飞的柳絮,看看你们还抽烟吧?也是,李老师现在是老师啊.怎么烟瘾上来。还鼓动学生抽烟啊?贾伟把一撮柳叶大的转莲叶子在手心里一搓,就拿起那个他用吐液缝制的白纸喇叭,用一只手心端好了转莲叶,对着喇叭口一点点地往里窜,转莲叶子像一粒粒黄米,楚楚地流进筒里。贾伟非常娴熟地把纸口用大拇指,食指.中指那么一捻.大概有五六个三百六十度的转转儿,纸烟筒在手心里滴溜溜像个滚筒,摩擦着他的手心蹭蹭地转.转好了转结实了,用指头使劲一掐那拧的纸念儿,把略带黑色的纸劲儿念儿往脚边一扔,一颗纸烟就卷成了。我瞅了瞅在那里骨碌的纸劲儿念儿,瞅瞅头上的垂柳丝,想,来一股风吧,别让他们抽烟了……呼啦——真的来风了。我差点拍手叫好。贾伟这颗烟MJlI目II递到老师手里,话还没说,就看到脚跟的白喇叭顺着骨碌碌跑,他连滚带爬地追开了。我和老师一顿大笑。后来,烟成了他们俩的必备之物,不吸烟,就像不吃饭一样。那晚,我似睡非睡间,李老师用发黄的手撸我的额头一下,是不是又以为我在感冒发汗?那股烟味儿在我的鼻息间飘动。我猛然抓住他的手,眼角溢出泪来,老师,你来了?我发现他的眼角眯成一条缝儿,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角儿眯成缝,是在我的预料中的,老师他近视。老师在我发烧的病榻前,眯着眼看,是一种慈爱罢了。但.我猜测他近视是错的.在后来的武装部军检中,老师他并不近视。他只是一种菩萨心肠,一种善意的笑。我再没多想什么,只是那舒缓白皙的额头,令我感到异样。感到一种心酸和眩晕老师——别走!我蓦然醒来,觉得我的头都晕大了!记得那个凌晨天上还布满星星,公鸡叫个不停,闷热的大气压把飞蛾、小虫聚拢在一起。紧紧地合抱着。手电的光束几经暗哑,但还能映在脚下柴草丛中的露水之光。白天,李老师找到我,大林,我们去班吉塔吧,你三叔的活计忙不过来,帮帮他。我三叔是谁啊?就是贾伟。我们三人光屁股长大,穿着兜兜儿上学,弹玻璃球,打片几,拿着弹弓追小鸟。志向不同,老师在经济大潮的催动下,他不满足那36元钱的工资,在校长百般挽留下.还是随我们中学生一起毕业了。我们商量了怎么F海,怎么开辟一番天地。贾伟在村中辈分大,我叫他三叔。他很有号召力.他也对我们说过:你们想出去打工。我不反对,但我认为,怎么干也是给别人干,我就想自己干!嘿嘿,李老师天生抬头纹重,眉头一皱,都拧到一起.像系个大疙瘩:能行吗?我鼓励说,试试吧,不试,怎么行?我这话非常管用,这就是后来把贾伟我三叔打造成包工头的主要因素。三叔开始把自己家的树都放倒了,用锛子斧头砍木橛、用锯锯卧牛子(插砖墙,盖房用的)、顺水子,钉马凳。什么盒子板.翘板,弄了满当院。之后,他请我们喝散啤酒,抽大公烟。他照我们的肩头擂着:你们帮我大忙了!我说,我也没帮什么,我干活忙。李老师说,部队的煤天天得装车,就是挣的太少,一块五毛七,还不够买一双胶鞋。是啊,我瞅着我们黑得发焦的破胶鞋说,这个破煤,还呼呼地着火。三叔没干,三叔笑着说,听说你们在煤里烧地瓜吃?哈,老师笑了,我们在站台运到锅炉房回来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地瓜.你馋名家近作>>LIAOHE了吧?我说,那也不好,装车烤死了,我们都要烤成地瓜干了。我们多咱给你干?三叔没言语。他心中没谱。他叹了口气,明春有活吧。老师说,我看他们当兵的真好。闲的时候,写个小说。哈哈,还想着写那个?闲心!当兵的好吗?看电影还要一毛钱的票,怎么进得去大礼堂?哈哈哈,我们三个人都笑了。部队很少演电影,进不去的混子们不管那些,就远远地扔石头,往礼堂的窗户上砸,哗啦,哗啦——总响。我们三人却从主席台上毛主席和华国锋的大画像后面偷偷地爬了出来,消消停停地看《铁道游击鳓。我们是穿着的确良绿袄。帽子上戴着红五星钻进去的。李老师说,看不上,我们不看,谁也不许打玻璃。我们说是。我们进去电影没开演,怕查出来,就爬到台上。老师问贾伟,带烟没?贾伟不知从哪整了一盒大前门,老师乐了,眉结又打在一起,好烟,好烟!我说老师你的小说写啥样了?你别再叫我老师哈!怎么又提小说?你不是说写小说吗?我是说当兵时闲着。老师再就默不作声。他回去一定想我说的话了,是不是激起了他的兴致或灵感。一天,老师对我说,大林,贾伟一心就想着当包工头,这个志愿很好。你是不是还喜欢文学?我们考不上中专,主要是数理化不行,我们在中学一个劲地蹲级,也没学会数理化。让语文这个坏东西给耽误了,有时我真想骂它一顿。即使这样,市里寒假要举办文学讲习班,我们去学习一下好吗?得多少学费?十块钱。啊?这么多?你没有,我可以给你掏上。你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以后还你!我们一齐去的市文联。半个月,我们吃住在一2起,花他的钱多一点。我们的感情不一般。有一次,认.o识他的几个老师,请他吃饭,我也和他们同桌,让我@翼靠墨蓑嚣耗等篓茹裟竺型筹篡袭案怎么这么说呢,我只是喜欢诗而已。是老师替我解了围。他们都哼哈地答应着,抽烟,敬酒。有个小白脸,我不喜欢,甚至厌恶。老师后来说,只是认识一下,何必较真儿。那个人在席上,就是管‘‘艾青”叫“艾(yi)青”,我们谁也犟不过他。回来后,在第二年秋.老师光荣地应征入伍了。他的小说也没写成,他说,社会经验少,怎么也写不好。等到了部队,体验一下生活再说。哈,我笑了,我怕是文字都得就饭吃了。人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几个,偏偏就在语文上整了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贾伟说,我们有力气,怕什么!就豪迈地唱起了: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我们就跟着唱: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再往下就是笑,就会这一句。下一句不会了。毕竟我们是一群农民的儿子,像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那是嘴到音出,不带磕巴半句的。我和老师去班吉塔帮三叔打地面是在老师押运回来。老师在班吉塔当的兵,那里是沈阳军区的,一个后勤哨所。他们在火车上押运,车上装载着雷达去的南方,老师大开了眼界。老师当的军种,就是天天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山站岗,刮风下雨,他没叫过苦,他说,最苦的,就是他不能抽上一颗烟,有时难受得他想哭。哨所里是不许抽烟的,里面的山洞装着过了时的炮弹。他还兴致勃勃地说,我们每年都要在很远的深山里毁一批炸弹,真过瘾。国家和平了,毁些炸弹算什么?你就那么憋着?他的烟火在天亮前的夜空中一明一暗,一边走,一边说。嗨,那三年真叫苦啊!当我出来到村中.看到那个大伏天,臭臭爬满墙,人们点火烧,那个烟熏火燎的烟雾,我馋烟馋得眼泪就下来了。三年了,你也该戒了。我们都没说媳妇.要是说了媳妇,也不让抽的。老师说,我就嗖嗖地往商店跑,像去抢烟一样。第二天,我们在朝阳二十家子下车,路过一片红艳艳的高粱地,爬上了一座绿油油的高山。老师说.爬过这座山,就是我们的营地了。老师现在是个小捧长。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老师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全村人的光荣。在信中,贾伟知道通往班吉塔部队外的一段路要修,他是搞工程的,他十分上心这点事。这些年,他带领村里人致富,和他一起干活的人都成了万元户。我知道,贾伟脑瓜活络,也不是黑老板。贾伟就对我说过,都是本乡本土的,挣了钱大家分。他更深的一层意思,也对我说过,有了这一帮人,你才有钱挣。你有活了,找不到人干,钱是挣不到的。有人有世界啊!啥.他说的话,蛮有道理呢!我撤了一下嘴,你不愧是语文尖子啊,很有逻辑!三叔也没有长辈的材料了。他手里攥着卷尺,唰一下.抻出来就要抽我。我就跑着哈哈笑。我们干到半月有余,几千平米的路基都铺满了大石头,用轧道机压实。还没轧完,司机有天没来。谁也开不了。不知道李老师(我们叫他排长)怎么就过来了,贾伟搭讪:我的排长大人,光临指导啊!贫嘴!最近老百姓有人来找过,大家注意点。我们一下予就知道了.下面村中有一个跳蚤,要来争活干。{|长看看轧道机停在那,问:怎么没人开?贾伟说,谁会啊?排长你开开?捧长摩挲过汽车,他想,也差不多吧。他登上车,那么一鼓捣,车真像老牛一样慢慢地吭哧着起步了。地下的石块像见到上级领导一样,点头哈腰,俯首称臣。等他放下那上万斤铁砣的轧道机,那铁砣还在往下垂,地球是有引力的!我们这些语文成绩差不多的人,怎么知道物理变化?所以,谁也不在意,谁也不会用心去琢磨它。整个一个秋季都是那般闷热,偶尔从西伯利亚刮来一股寒流,有那么点凉意,却在饭食里吃出臭臭,那里的榆树浓浓密密,平时臭臭和古铜色的甲虫的呜呜声,不绝如缕。像远山庙里的隆钟。这还不算,我们一去时.水土不服,除了拉稀就是呕吐。我呢,睡电褥子睡不了,闹得牙齿肿胀,嘴唇起泡化脓。贾伟就吩咐厨房的师傅对小米过筛,严格把住虫子进入米里这一关。那天闲下来时我张着抹了土色药粉的嘴说:三叔,你说这个破地方,李排长怎么当兵啊?贾伟打趣地说:你的嘴还是不疼啊,国家的每寸土地都要人保护,你没去过大西北,没去过边防,那个更困苦。在村外。我看到贾伟偷偷地买了盒烟,点着了明明灭灭的火。我说:三叔。哨所里不让抽烟。贾伟白了我一眼,咳嗽着,烟圈顺着嘴吐出,哧溜——钻鼻子里:我是在外面抽,你看我在里面抽过烟?我愤懑地说。你们啊,好席烟民。这时一股浓烟在村庄外面升腾,我们都朝那个方向望去,那就是李捧长说过的.百姓在烧房屋前脸墙上的臭臭呢。天凉了。臭臭扑到被太阳烤晒的热融融的白色光面上,黑压压全是。它们凝聚着一种力量,一种抱团的精神,如一颗颗钢钉,想透过培体钉入室内,去室内过一个冬天,它们要冬眠了。那天秋雨绵绵,整个大青山笼罩在雨雾中。忽听一阵大吼,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贾伟就从工棚里往外跑,一看傻了眼。村中那个跳蚤领着一群人和我们打到了一起.他们不让我们干活。当时我是被打糊涂了,脑袋流了血,后来听说,贾伟抱着我找车,在南票医院给我包扎的。回来贾伟就喝酒,抽烟,发疯般地要干死那个跳蚤,皮兜子里揣了一把菜刀,闯进了跳蚤的家。李排长带领一班战士把贾伟抓了回来。给他关在小屋里,他还骂。排长说贾伟,事情已经出了,我们要好好解决。我们都是一个村的,自然有点活就是向着咱们自己人。你想想,反过来,你住在这里,有活让外地人干,你会啥想法?直说得贾伟一声不吭。那天,李排长对我们说,这下好了,F一个工程来了,哨所外两边要各盖一座小楼,和村庄的老百姓一家一份。我因为脑袋的问题,在工棚里修养。突然。听到工人们在哨所外大喊:救火啊——失火了——我吃了一惊,一个鲤鱼翻身抱着脑袋就往外跑,那可是部队哨所啊。我看到一伙人都往工地里打的井旁边跑,心里有了几分安全感,这要是哨所里着火,方圆百里都会爆炸,那哨所的洞库里放的全是炸药啊。可我心想,奇怪了,井下会着火?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我们盖小楼那帮人包括村里盖楼那帮人都往一眼井跑过去,尽管围得水泄不通,我也看到了顺着人们挖挲起来的头发和焦虑的脸庞的缝隙里冒出的滚滚黑烟,把所有人都熏得咳嗽着,吵嚷着……我差点一个跟头栽过去。有人扶我进屋时,我脑袋嗡的一声,失去了知觉。听到一个女孩说,他的脑袋本来就受伤了,还逞能。再就听到一阵吼声.让我下去——让我下去——谁的声音?我怎么爬也爬彳i起来,这声音依然很熟。是老师,不,是李排长。接下来,我的脑袋混浆浆的,像灌了123汤,一片哭声在我的耳边回响。我知道出事了,我怕是死了……当我昏迷了两天一宿醒来,一摸脑袋,脑袋还在,看看伺候我本村的在我们工地做饭的女孩,急忙问:我昨天是不是摔坏了?李排长在哭我?我抬眼就看到了她红肿的眼泡,想不到她痛苦得说不出话来。我用尽全身力气支撑着床板,床板吱嘎嘎响,喉管里声嘶力竭地吼出一句话,手死死地扯住她的衣袖: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女孩的头晃动得像拨浪鼓,泪水已经淌满她的№ o∞0▲⑦
上一篇:腻歪的晶胞 下一篇:没有了